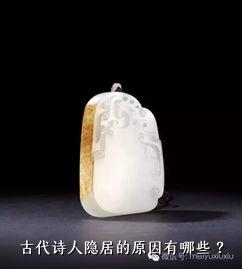1.有本小说主角能看透玉石,后面开了个珠宝店

《万事如意》
家无良田,家无厚土,只有鉴宝异能在身。
弟弟妹妹很担心,老母亲是最好的,有一只上流阶层的敌人。
将军少子、高贵公主、皇帝也来了,很热闹!
乱世大唐,治国安家,意外有她吗?
作为原生态大唐土著小妞
玉如意觉得鸭梨很大……
“上帝,你在玩我吧? ”
2.古代诗人隐居的原因有哪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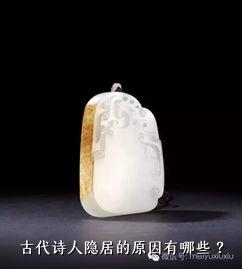
古代文人隐居的原因和目的多种多样,但总体来看,积极隐匿的只是少数,许多文人被迫隐匿,不得不进入山林。 诗中的僧灵一针见血地指出:“逢濑尽道休官好,林下为什么见过一个人?” (《东林寺酬韦丹刺史》 )这话说得有点过分,但也难怪。 古人隐居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本性使然:性本爱丘山。
虽然真正只为山水而隐居的文人并不多,但也不可否认,美丽的山水,尤其是隐居山水中的闲居生活,确实是引导文人隐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方面,陶渊明是典型的。 他在《归园田居》中说:“至少没有俗韵,做爱爱丘山。 不小心坠入网络,去了已经30年了。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诗人视大自然为自己的古林、故渊,视官场为罗网、樊笼。 这种天生的热爱自然的性格成为促使文人隐居山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敦煌文献中找到《山僧歌》 :
山居怎么好? 时间高,睡得早。 山中嫩草以为衣,斋食松柏随时饱。 躺在悬崖上
壁龛、石枕头、抱着乱草当上衣。 如果之前有狼籍生的话,一阵风从一开始就来了。 躲在山里,真光滑
路,更多的事情没有混乱。
住在山林里,衣食足,无忧无虑,打扫卫生也由山风代劳。 再看张养浩对山水隐居生活的描写:
云来山好,云去山好如画。 山是云倒霉,云与山同高低。 倚杖起云沙,回头看
山里的房子。 野鹿眠山亭,山猿戏野花。 云霞,我山很珍贵。 看着时光的流逝,云山也爱着我们。
(《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退隐》 )
向来为功名惹事,如今却忘了山水名利; 平时是利用鸡的声音朝早上走,现在快到中午还留着。
突然睡觉。 往常秉笏立丹墀,今菊花朝东簖; 平时向当权者跪拜,现在自由拜见
知道; 虽然总是有犯转移拐杖罪的危险,但现在便宜了,课在雪月的问题上开花结果。 落雁
带着胜利的命令”
第一首曲子采用连绵配对的形式,将“云”和“山”两个字放在适当的位置反复吟诵,表现出流云的音韵美和诗人对青山白云的爱。 这两者互相交融,相辅相成,勾勒出一幅美丽祥和的隐居生活图画。 人爱山,山爱人,山相融,物我一人,真的不知今夕何夕! 后者运用对比手法,将“往常”的仕宦生活与“今”的隐居生活进行对比,使读者强烈感受到山林隐居生活的闲居与优越。
(二)科举考试失败,只能蒙混过关)活下去没有意义,明早会放空炮。
古人读书的最初目的,几乎都是为了治国安民,治理光宗耀祖。 但由于朝廷能为读书人提供的官职有限,许多读书人没有“腹带”,只能无奈地逃到山林里去当隐士。 这部分人的心情相当痛苦。
唐末有个诗人叫任蕃。 他家住江东,在长安走了几千公里报考,结果落孙山了。 那种痛苦和绝望的情绪可以在他通过后对主考官说的话中看到。
下仆本寒乡人,不远万里,手遮赤日,步来长安,不能取首荣父母。 侍郎不会吧
听说江东任蕃,家贫苦闷,忍着让他去如来的日子? 以后如果敢辞职,就弹钢琴自娱自乐,学道自娱自乐。
(《唐才子传》卷七) )。
西藏作为贫穷的读书人、使徒
步往返万里应考,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他满怀希望而来,结果空手而归。据说,主考官听了他的这番话后很惭愧,想挽留他,但任蕃执意离去。他后来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不甚清楚,但根据他的最后一句话,大概是当了隐士。
罗隐是唐末著名的诗人和小品文作家,他一生的经历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积极进取的文人是如何被迫当了隐士的。
早年的罗隐抱负远大,想通过科举进入朝廷,做一位“执大柄而定是非”(《谗书·重序》)的名臣。据史书记载,罗隐从20岁时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一直考到55岁。在这35年之间,他10次考试均遭失败,不得不浪迹天涯而一事无成,这种非常人可以忍受的坎坷遭遇对罗隐心灵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他写过许多诗歌来表达考试失败后的失望和羞愧之情,他深感近对不起师友,远有愧于古人,甚至面对妓女也觉无颜:
罗隐……初赴举之日,于钟陵宴上,与妓云英一绝。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
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耶?”隐内耻,寻以诗嘲之:“钟陵醉别十
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见俱是不如人。”(何光远《鉴戒录》
卷八)
朝廷不要罗隐,男子不要云英,罗隐抓住这一相似之处,勉强与对方打了一个平手。作为士子的罗隐,竟然与妓女较起真来,可见他对自己屡次落第的羞愧和敏感。在社会上处处碰壁的罗隐突然想起了庄子,他写了许多诗歌,用庄子的万物一齐、无用之用来进行自我安慰。虽说如此,他还是感到屡屡落第使自己难以在社会上抬起头来,于是他便脱下青衿,换上道袍,躲到深山老林中隐居起来了。
由于种种原因,像这样不得不当隐士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可以说,每一位看似潇洒的隐士,怀里都揣着一本辛酸账。
(三)惧怕灾祸: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因此上功名意懒。
元代的张养浩把因惧怕灾祸而隐居的心情写得十分明白:
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
遭难,把个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双调沉醉东风·班定远飘零
玉关》)
这首曲子一连举了六个历史事例:班超武功盖世,屈原忠诚无比,李斯功居第一,陆机名闻天下,张柬之老谋深算,苏东坡天才绝伦。然而由于他们都曾涉足官场,结果有的飘流四方,有的临刑长叹,一个个搞得灰溜溜地难以安享天年。既然如此,有吃有喝的何必进官场去冒风险!元代的任昱和明代的陈铎也以同样的理由提倡归隐:
南山豆苗荒数亩,拂袖先归去。高官鼎中鱼,小吏罝中兔。争似闭门闲读书!
(任昱《双调清江引·题情》)
仿邵平种瓜,学卢仝煮茶,喜春雨全禾稼,数椽茅屋近鸥沙,志不在陶朱下。诗
酒关情,琴书消暇。放会顽,撒会耍。黄金印手拿,琼林花帽插,祸到有天来大。
(陈铎《中吕朝天子·归隐》)
这些文人不是不想手拿黄金印,帽插琼林花,只是感到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个个都好像锅中的游鱼、网中的小兔一样,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别人吃掉。他们担心踏入仕途后,终有一天会陷入政治纠纷,脱身不得。这些隐居之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那些达官贵人呢?张可久有一首《双调·庆东原》:
门长闭,客任敲,山童不唤陈抟觉。袖中六韬,鬓边二毛,家里箪瓢。他得志笑
闲人,他失脚闲人笑。
这些隐士是带着一种看达官贵人笑话的心情躺在深山老林之中的,他们的这种心理未必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标准,却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平衡心理的方法。
(四)厌恶官场:一家富贵千家怨。
官场黑暗,自古已然。看不惯黑暗的官场,是士人隐居的另一个原因。如元代的蜜兰沙,就属于这一类的人。明初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卷四《谈薮篇》中说,蜜兰沙在元代至顺年间任福建廉访使时,曾写了这样一首《游仙诗》:
刀笔相从四十年,非非是是万千千。一家富贵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
袍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事,云在青山月在天。
这是一位老官僚对自己官宦生涯的沉痛追悔,他认为一家的富贵是建立在千万家的怨恨之上,自己的半生功名实际上是半生的罪孽,于是他要放下牙笏,脱去紫袍,进山去当隐士了。当然,像这样因内疚而弃官归隐的人是非常少见的。
(五)终南捷径:今之隐也,爵在其中。
“终南捷径”是一个有名的典故,故事发生在唐代诗人卢藏用和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的身上:
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佳处。”承祯徐曰:
“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愧。(《新唐书·卢藏用列传》)
卢藏用是一个一心进取的人,但仕途不利。为了博得更大的名声,取得更高的官位,于是他就隐居起来。终南山接近都城长安,少室山接近东都洛阳,于是他就把自己隐居的地点选择在终南山和少室山,所以当时的人戏称他为“随驾隐士”。后来,卢藏用通过这条“终南捷径”,也真的进入了朝廷,累居要职。
另一位通过“终南捷径”进入仕徒的是宋代著名道士种放。种放是河南洛阳人,父亲和几位兄长都当过低级官职,而种放却与母亲隐居于终南山。后来,“隐”出了名,得到了钱若水、王禹偁的举荐,受到朝廷的重视。他多次奉召入朝,宋真宗也多次赠诗以示宠幸。《渑水燕谈录·高逸》说:“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垂手援放以上,顾近臣曰:‘昔明皇优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种放号称“高逸”,但他真是一个淡薄名利的隐士吗?回答是否定的。他不仅接受了朝廷的官职,而且对利看得相当重,《宋史·隐逸传》记载:
(种放)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至争讼,
门人族属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尝乘醉慢骂之,嗣宗屡遣人责放不法,乃条上
其事。……续给其俸,然犹往来终南,按视田亩,每行必给驿乘,在道或亲诟驿吏,
规算粮具之直,时议浸薄之。
这哪里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隐士,分明是一个欺行霸市、横行乡里的恶霸,以至于有人在皇上宴请种放时,“诵《南山移文》以讥之”(《宋史·隐逸传》)。
种放也是因为早年科举不利才寻求“终南捷径”的,而授予他这一妙方的是另一位著名道士陈抟。《渑水燕谈录》说:
种放明逸,少举进士不第,希夷先生谓之曰:“此去逢豹而止,他日当出于众
人。”初莫喻其意,故放隐于南山豹子谷。真宗召见,宠待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
其言。
文中说的希夷先生即道士陈抟,南山即终南山。陈抟不仅指示了他仕宦捷径,甚至连隐居的地点都为他选择好了。住在终南山,既有隐士之名,又接近长安、洛阳、开封一线,易于为朝廷所知。隐居地的选择,也是一门仕进的学问。特别是文中说的“他日当出于众人”一句,说明当初隐居时就已经规划好了博取名利、出人头地的目的。
当然,走终南捷径的人并非个个都能够像卢藏用、种放那样幸运,也有人“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这条捷径上栽了跟头。《新唐书·杜如晦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杜)淹字执礼,材辩多闻,有美名。隋开皇中,与其友韦福嗣谋曰:“上好用
隐民,苏威以隐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为不仕者。文帝恶之,谪戍江表。
杜淹早就知道这条捷径,可惜在走这条捷径时,没有藏好自己的“尾巴”,被隋文帝给抓住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官场,反而被流放到了江南。在古代,像这一类的假隐士为数不少,故皮日休在《鹿门隐书》中感叹说:“古之隐也,志在其中;今之隐也,爵在其中。”《新唐书·隐逸传》对这一现象也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论述:“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宦捷径,高尚之节丧焉。”
在现实生活中,隐居的原因要比以上所述复杂得多,比如因亡国而隐居的,为修道而隐居的,等等。关于这一点,在其他章节中也有涉及,此处不再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