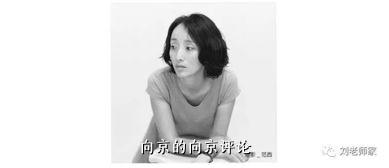1.向京的向京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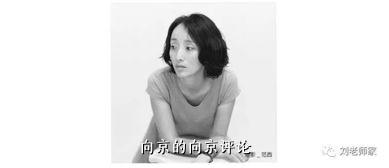
到北京的人体作品,最终只是再现和表现,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人体写照。 但是她们是关于什么形式和内容的再现?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人文学家盖尔魏斯(Gail Weis )指出,所有的身体都属于统一的参照系和标签。 “这个”的身体或者“这个”的身体的图像不存在。 事实上,当我们提到一个特定的个体的身体时,它总是与普遍化的身体标准或参照系相对应,例如,一个拉丁女人的身体;一个母亲的身体; 女儿的身体; 朋友的身体; 性感的身体; 老人的身体和犹太人的身体等。 [1]于是,如果前往北京的女性的身体不是“特殊”的身体,或者像韦斯指出的那样“真实”的“基本”的身体,我们怎么应对她们? 我们的反应和她们的身体之间会产生摩擦和错位,在出生的体内引起蕴藏的张力。 它反映了艺术家应对女性身体“真实性”的努力。
超模的身体,也就是所谓的理想身体形状,即使是超验的,原本也不是存在的。 现代文化中非典型女性身体图像的表现成为公开的尝试。 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对女性审美的挑战,在我看来,向京似乎想通过她的作品来超越主观的、“旁观者的眼睛”的争论,阐发女性图像再现的本质。 正如朱迪思巴特勒所讨论的,女性——的女性象征和职业生涯——不是不变的固定概念。 对巴特勒来说,对这种概念的理解只是“基于作为特殊语境下社会构建对象而理解性别的历史人类学位置”,“构建的性别概念被理论化为从生物学本质上独立的性特征后,性别本身就成为自由浮动的战略”、“标准的女性/女性” [2]这并不是关于向京作品表现雌雄同体、消解性别的作用,但却为摆脱固定生物学意义性征的女性主义思维提供了新的借鉴模式。
——摘自2008年Norman Ford 《全裸:向京的不平静的身体》
“通过身体说话。 ”对北京的最初选择与今天女性主义的集体方式没有变化。 但是,她对“女艺术家”的标签很反感。 这仿佛已经意味着歧视,意味着“钉死女性血肉的蝴蝶”的暴行。 但是,如果不是以这种显而易见的女性主义理论为背景,没有“第二性”的文化命题就会充当反抗与抗争的藩篱,她的创作意识和作品效果就不会那么明显
北京经常把这部作品自称为“第一人称”的作品。 这个第一人称的意思是她完全强调主观的创作观点。 换句话说,这就是她思想和感情中的女人,由一个女人创造出来的女人,侧重于女性力量的表现。 这一形象与男性对女性的审美期待相反。 根据女性主义的分析,在这个性别平衡的世界里,有所谓决定性的男性眼光,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到女体上,女体就有了相应的风格。 在传统的展示角色中,女性被看、被展示,外表被规定具有视觉和情欲的冲击力,可以说这意味着她们被“看”。 在这部作品中,“被看”作为形式的道具被保留下来,作为反击的利器被巧妙地使用。 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女人,但不包含一丝色欲感……这是将心理竞争还原到视觉表层的创举,因为在男性的观察中,女性的口罩和逃避不仅是必须的,也是观察的中心。 看到一个女人在自己面前层层伪装,放弃最后一道防线,是色欲和权欲相结合的男人的快感。 在这部作品中,女性以放弃任何隐瞒和逃避的“被动”方式,诡谲地全裸,客观上打击了男性的色情消费。 其力量在于拒绝性观察,本身就是绝对的存在。 其效果的获得取决于其自身的形象是性“零度”还是中性倾向。 像——史前神话中创造的第一个女人一样,还没有置身于两性人的现实中,没有两性人的意识和体验,无明不白地执着着的,只是生命体。 而那超常的身体量所形成的压迫力,要么是女性原初生命力的暴露,要么是被男性——男性化的结果
实际上,自我封闭的解脱途径是转向客观世界,通过对现实的经验和感知获得姑息治疗。 “他人不是地狱”。 波兰现代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这样写道。 “如果在黎明时分,/他们的眉毛被梦洗涤后/能瞥一眼他们”。 (010 ) 3010 )或者,在北京深受喜爱的德国诗人里尔克的诗句中,“跨越这两个王国……在这两个王国中征服岁月。 》(《另一种美》第一首)内外,超验与经验,设定在梦想与现实的境界,是我们必须跨越的魔障。 人性中丰富共同部分感情的发现,即使不能消除自己本质上的孤独和痛苦,也还是一种真实的慰籍,并有助于消除个人精神的狂暴色彩和夸张的牺牲姿态,让我们冷静理智地看待自己的痛苦,让这种痛苦成为人类普遍处境的去北京的《杜伊诺哀歌》(2006 )
主题上正彰显了对于客观世界的接纳意识,而处在对于客观世界逐渐敞开的情感状态之中,自我的焦虑慢慢减弱,代之以深阔起来的体验。她意识到,“静静地去看一个灵魂,是重要的”,在每一个身体、每一个灵魂那里,无论是那种“我22岁了,还没有月经”的奇特类型的女孩,还是《秘密的瞬间》(2005)之中的那种在街头偶然瞥见的老年女人,都蕴涵了生命的神秘和存在的奥妙,在向京对于她们所作的观察、冥想与表达之中,“女性身体”这一主题已然超越出自我的青春期体验,进入到更为冷峻深邃的现实深处,而她对于自我的反观或者说对于自我封闭的表现,则来得更为超然与准确——《寂静中心》表现了一个女人在手淫之中的那种奇特的自我满足状态,女人脸部的皱缩感来得如此生动而真实,这样的主题是一个过度沉溺于个人世界、拒绝长大的“女孩”所无法谈论和面对的,惟有一个成熟的母体才可以作出这样果断、干净利落的分娩。
从这件作品(《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之中,我们看不到性别作为一种尖锐的批判意识所起的作用,相反,女性本真的气质与情感得以被显明,那是一种从表面上看去显得脆弱、温柔、忧伤得令人心碎的阴性气息,然而,这并非第二性的“奴性美感”的表现,而是一个摆脱了欲望和喧嚣、趋向了平静与梦想的世界的原型,类似于容格所言的“阿尼玛”,它与其所对应的“安尼姆斯”一样,存在于我们每个生命的本身之中,如果说安尼姆斯象征了阳性,象征了现实与行动,权欲和野心,阿尼玛则象征了安宁与梦想,沉默与守护,一如法国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在他的著作《梦想的诗学》中所言:“任何男人抑或女人,从‘梦想的斜坡’往下走,一直往下走时,都能找到他在深层的‘阿尼玛’中的安宁,这是在往下走而非往下坠落。在这一未确定的深处是阴性安宁的天地。正是在这无忧无虑,无野心,无方案计划的阴性安宁中,我们得到了具体的安宁,使我们的全部存在得到休息的安宁。”
这种阴性的安宁,在向京的这件作品之中通过水这个隐形的意象得到了强调,而水无疑是阴性最为典型的象征,它荡涤我们的欲望与焦虑,它的“存在“构成了安宁与温暖的源泉;在中国的古老哲学中,它更是作为至善的象征(“上善若水”,《老子》),时间的隐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征服一切的力量(“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摆放于作品中心的脚盆正如一座井台般象征了水的存在,事实上,这件作品的形式张力正在于日常生活与精神仪式的混淆,它近于一个聚焦不准的镜头,滑动于这两者之间,将两者的特质赋予了对方——日常被赋予了仪式的尊严,而仪式被赋予了日常的形态。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一种精神能量在现场的流转,仿佛在述说超验与经验的界限被打破,它们已经相互叠合、交融为一体。
不过,这个界限仍然是在女性世界的内部被打破的,这件作品中的圈形仍然属于一个视觉化的心理魔咒,一个典型的自我封闭的结构,只是这个“自我”从女性的个体被扩展成女性的集体,对话和交流在她们之间成为了可能,但是,她们以群像的方式,以那种背对观众的姿态,再一次地,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地强调了向京已经说出的那一切。
——摘自2008年朱朱《魔戒的内部》
向京以前的那个自我,存立于对象之中,以静静的凝视与痛感的抚摸,与之融为一体,如今,她似乎有意要撇弃那份天才的感性,如同舞台剧导演般操纵一个结构化的整体,换言之,那些被创作出来的演员和动物更倾向于作为意象而非单个的作品,参与到空间整体的营建之中,同时,被预估在内的还有观众的目光与身体,他们将徜徉、往返于这个展示空间,寻觅有关自身处境的隐喻——在她的工作室里,我目睹了展览方案的沙盘,除了分布在展厅里的作品,还有一道沿墙悬挂的巨幅舞台帷幔,和上下盘旋的通道……它们共同营造着一个带有剧场感的氛围,一个由艺术家本人布设的“全景敞视空间”。
事实上,这是试图创作一个展览,而不是满足于仅仅创作一些单个成立的作品。我猜想,从一开始她的构想就受到了预先确定的场馆实地的影响。这个美术馆的空间在她的头脑里盘旋与反复被掂量,以致成为一块“私人的领地”,一个秘密的王国,其结果是她决意要身兼数种角色——成为艺术家:创作这些作品;成为策展人:以空间对这些作品进行进一步彰显和“治疗”(英语中的“Curator”正是从“Cure”而来);以及,成为这个展览的阐释者,将观众纳入到一个既定的思考维度中,而最后的这个角色的担当,也许显示了她的一种焦虑,即她意识到自己的作品与表达意图之间,隐含着一种可能的裂隙。
的确,杂技的存在本身包含了“扮演”正如动物的存在本身包含了“被围观”,不过,她这两个系列的创作本身并非充分围绕这一表达重心展开,现场的格局或许能够对此作出强化;如今的这些作品中真正感染我的东西,仍然与她一贯的天赋、视角与情感息息相关——如果说,她想要使这个展览成为一个寓言式的图景,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它仍然是一个童话式的奇境,或者说,是一次童话与寓言之间的滑动。
从杂技表演的技能元素之中,向京抽取了“托举”与“柔术”两种,从造型上将它们进一步加以夸张,期图观众能够从那种不可能的造型姿势里读解出杂技的“反人性”的一面——那是一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以及,以身体作为表征的自我的迫不得已的扭曲?这一题旨确实可以从她的创作中被窥见,譬如,在高耸的“无限柱”里,每个女性双腿翻转至身前,以不可思议的柔韧之躯来承受层叠其上的重力,面孔上保持着表演时所需的微笑。这种微笑多少显得僵硬、空洞,掩盖着生理性的巨大压力;而在“四人组合”中的造型之中,位于下方的演员身体的受力点被构思得格外诡异,在现实之中几乎不可能实现。
“世界上不流泪的人中间,没有人比我们更高贵、更纯粹”,在创作那件有关海象的作品《唯岸是处》的过程中,她引用了前苏联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来为之定调,也许这样的引用多少显得夸张,但无疑显示了她标举精神性的强烈欲望,归根结蒂,动物的存在指明了生命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宇宙的神秘力量;而它们在现代世界受到的威胁反过来可以指代那些试图坚执于精神追求的人所具备的流浪感,这些形象一如后者的孤独的灵魂的化身。这里,我再次想起被向京经常挂在嘴边的“老灵魂”之说,在另一次访谈录中,她谈论到:“在丧失生的尊严之前完成那还优美的纵身一跳……知生死的都可以叫‘老灵魂’了”(见《女性的自在》,原载于《今天》杂志2010年第四期),而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那种在经历沧桑剧变和摧毁性的打击之后、仍然留住了爱与希望的心灵。
在对于“动物”系列的凝视和思考之中,我们会淡忘社会处境的具体内容而深化了对生命本质(以她的话而言,即“人的自然属性的部分”)的体验,而她最初设定的“被围观”并非我们凝视的重点所在,相反,是我们感受到了“被围观”,被这些单个的、茕茕而立的形象逆向地检视与盘诘着,尤其是当我们置身于那匹马的面前的时候。
社会学或者集体性自我的主题表达,惯来构成了对于我们的艺术家们的诱惑,而向京在经历了个性化的女性题材表达之后,也试图迈出这样的一步,从某种程度上,这是走向了她本来的对立面,而趋近于当代艺术的观念性操演,而她亦意识到其中可能蕴含的危险,她试图通过结构性与暗喻的方式来避免当代艺术中常见的、对于社会学主题的二元对立性的简单化处理,给出一个折射性的意义空间。
对于艺术家而言,以往的那个自我亦是物,而自我超越的雄心有时亦会是一种物化,但是,以艰苦的创作主动地挑起自我的“心物之争”,至少可以赢得“正见”的机会;循沿这样的方向且能每以反省的态度观照内心,就不会担忧短暂的迷失,而自身之中最好、最明净动人的部分也将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就像向京依照《山海经》中的传说所塑造的那一个动物“不损”(它的肉身不受刀斧伤害,随砍随生),迟早会和更为深切重大的精神表达结合在一起。
——摘自2011年朱朱《“心物之争”:童话还是寓言?》
2.中国有哪些比较有名的艺术工作室?

那必须得提雕塑家向京和她先生瞿广慈的。这个工作室在北京的艺术村宋庄,最大的特点是建筑体量又高又大+陈列的作品众多。首先,体量大的原因源自向京做的是雕塑、而且是大型雕塑。向京雕塑《你呢》向京雕塑《敞开者》,巨大雕塑的侧面向京雕塑《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小玉和雕塑的互动向京《